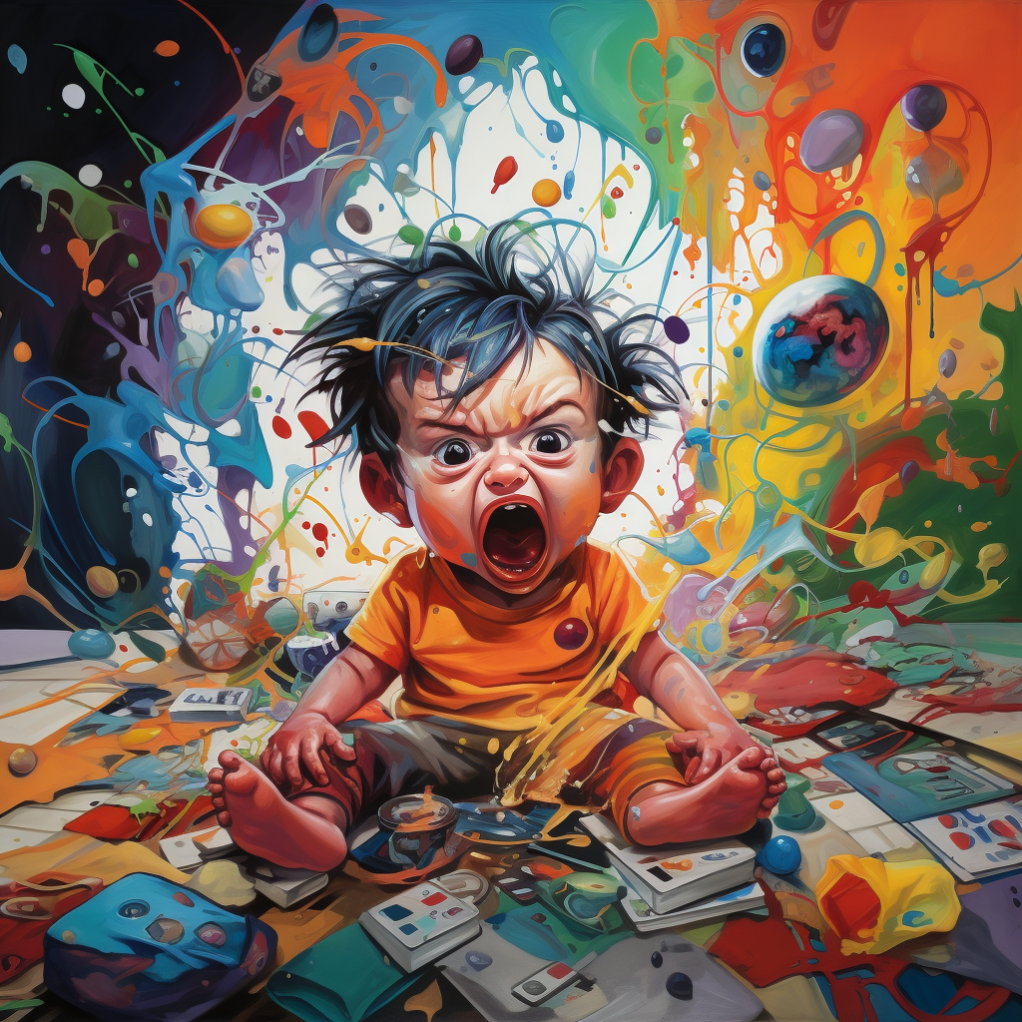死亡母亲综合症
不曾作为「我」而存在的空白
- 文 / 乔晓萌 英国塔维斯托克中心 精神分析研究 硕士在读
- 题图 / Midjourney
- 标签 /
Andre Green;死亡母亲;自恋损伤;
死亡母亲与自恋损伤
法国精神分析师 Andre Green 的「死亡母亲」(the dead mother)[1]指代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母亲,她们在情感上曾经在场,随后因为抑郁而撤离,母亲并未真的「死去」,对于孩子来说却也不曾「存活」,由此留下巨大困惑与空洞。(译文参考此处。)
《死亡母亲》一文最初发表于Life Narcissism, Death Narcissism(生自恋,死自恋)[2]一书之中,而非常见版本的 On Private Madness[3],可见它与自恋主题的紧密联系。自恋损伤常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死亡母亲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于婴儿的镜映缺乏,事实上造成了一种非常基本的原初自恋损伤。比起后期遭受的贬低、羞辱,这是一种彻底的否认、忽视,甚至是消除。这种损伤为生命奠定了一种迷雾一般的绝望色调,很难通过后来成就所弥补、调节。
「死亡母亲」这一概念的重要,首先因为自恋问题常处于治疗核心位置,正如 Meissner 在《偏执过程》[4]一书中指出的:
❝
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受伤的自恋的受害者。……所有这些病人都有致命的自恋的潜在基础,这是他们的病理根源。通常自恋的核心被很好地隐藏和保护起来。从治疗上来说,它是所有障碍的核心所在。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紧张的治疗努力来通过层层的防御,才能接近自恋,自恋位于障碍核心,为了保护自恋,其他的一切都得到了坚定的维护和保护。
另外,精神分析理论发展常与时代、文化变迁有关。譬如自体心理学的横空出世就与自恋时代强烈相关。特别地,这一框架尤其适合华人,也与东亚文化代际创伤之下的自恋损伤有关。与之类似,「死亡母亲」这一概念对于理解中国自恋损伤现象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死亡母亲概念扩展
即使 Green 原文之中更将之聚焦为母亲抑郁这一特定现象,但是,我们或许可以将之扩展成为由于种种原因而「情感上不在场」的母亲。因为种种之前曾经在育儿经系列之中提过的代际创伤,情感上不在场的母亲在中国文化之中是非常常见的。
母亲在情感上不在场或可分为如下一些情况:
- 母亲因为自己正在经历的丧失而抑郁(也就是 Green 原文之中所描述的情况);
- 母亲被自己的焦虑或者情感困难所占据,而没有空间为孩子在情感上在场;
- 母亲由于自身的自恋损伤,没有能力发展出来对于客体的关注,即使对于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
- 母亲由于缺乏情感支持而没有足够的空间抱持孩子;
- ……
我们可以再举几个更具体的与死亡母亲相关的例子:
- 母亲在身边睡着之后,孩子总是无法确认母亲是否「死去」,因此,总是希望通过「戳」这个动作确认母亲还活着;
- 母亲沉溺于家务琐事之中,无论孩子如何表达,母亲总是完全忽视,没有回应;
- 孩子展现出来过度活跃的特质,母亲却没有留意到此时孩子需要的更是一种情感回应,不断错过的互动之中,得不到情感回应的孩子却变得越来越兴奋,以期通过这种方式接触母亲,母亲则越发疲惫,逐渐木僵,由此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 ……
相关心理过程讨论
无法唤醒的母亲
关于「死亡母亲」,一个可以比对的是心理学上著名的由 Edward Tronick 带领的的静止脸实验(still face experiment):
❝
首先:视频刚开始妈妈和孩子之间正常互动,妈妈对孩子的反应给予热情回应。接下来,妈妈开始改变表情,由热情回应变为木然无表情。无论孩子什么反应妈妈的脸始终是静止、空洞无变化的,在短短 3 分钟时间里,孩子尝试许多方法:笑、指向远处、挥舞胳膊、大叫、哭闹,试图引起妈妈的关注和回应,在反复尝试失败后,孩子的表情开始变的无助、游离和痛苦……最后当妈妈恢复正常状态,孩子的情绪也很快恢复。
与之类似,Green 指出,死亡母亲情结之中,那些本应出现抑郁的时刻,较之于看似「正常」的抑郁反应与过程,个体实际上经历的是从来不曾放弃唤醒母亲的执着努力,以及这种努力得不到任何结果的巨大无力;与此相伴的是,即使获得某种成就,个体也永远无法感到满足,就像身处一个无期徒刑的鞭笞牢房,或者一直在坠落于永不到底的深渊;西西弗斯的比喻当然也可以用在此处,生命徒耗、空燃,都是类似的感觉。
母亲并未真的死去,她还为孩子留下一丝希望,但是,与此同时,她却不再真正存在。希望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东西了:那丝希望从未得到兑现,残存下来的是压倒性的的困惑、无望。个体将被卡在「通过某种努力唤醒母亲但从未成功」的绝境之中,永世无法翻身。
不曾存在的「我」
梅尔泽的著名概念美学冲突(aesthetic conflict),讨论的是,婴儿即使在感知层面上知道母亲的美好,但却无法了解母亲的心智;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存在于母亲心智中,不知道母亲心智是否由其他事物所占据,不知道母亲心智中的自己是否同样也是美好的。
了解母亲心智的过程本身也是自我发展的过程。只有通过首先存在于母亲的心智空间之中,一个人才能作为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在这个层面来说,唤醒母亲的努力只是为了「存在」而已。
死亡母亲相关的情境带来了一个近乎精神病性的环境:无论如何呼喊,没有人能够听到自己,自己与他人之间隔着一个难以逾越的沟壑,在体验上仿若并不存在。痛苦也好,成就也罢,无人分享,只能归零。在主观体验之中,这与在心理上、情感上被杀害无异;也是我们前面提过的原初自恋损伤。
这也是为什么他人的反应(reaction)对于一些人来说非常重要的原因,他们可以接受非常激烈的争吵,甚至争吵或将会使得他们感到一种特殊的「活力」,但是面对「冷战」,他们将会感到又被抛入了那个无人回应的深渊之中,甚至自己不再存在。很早之前,我曾写过一篇只有刺伤你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说明的是类似的道理。
以更为当代的理论来看,这也将会造成心智化能力的重要缺陷(可参考播客寻求一份心智地图),无法识别他人以及自己的情绪,而总是陷入不切实际的想象之中,因此总在情绪调节上有困难;并且有可能导致过度心智化的现象。过度心智化常出现在边缘或自恋人格中,他们可能会对于人际交往、对话或者面部表情做出非常细节的研究推理,从而得出并不符合事实的结论。当然,在我们讨论过静止脸实验与面对死亡母亲,孩子试图唤醒母亲的种种努力之后,或许可以看到,过度心智化实际上也是一种企图否认死亡母亲的事实,并且与之进行沟通的绝望努力。
「空白」与其主观心理体验
永远无法唤醒的死亡母亲在心理结构之中留下了一团难以填补的彻底决绝的「空白」,在体验上犹如一个无法逃脱的黑洞。这个黑洞通常甚至从来没有真正面对,因为生命之中的一切努力都向着逃离;一旦面对,将会永失生命之中的一切意义,只剩下「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使之更加困难的是,个体将会认同死亡母亲的「死亡」与没有活力,以至于这样一个「空白」难以转化,而很长时间作为心理结构之中无法支持的部分存在。
这一「空白」和许多主观心理体验相关。
空虚
这也是我们时常在严重人格障碍之中描述的「空虚」(emptiness)。这一感受非常常见,但实际上很难表达清楚。我们在这里试着对此进行说明。
回到前面所说的不曾作为「我」而存在,与世界隔着一个无法逾越的「壳」,无论如何呼喊从未被听到、看到——即使不在那样强烈的情绪之中,这也是一种长期、慢性地难以与他人产生连接,甚至难以与自己产生连接的状态。此处或可与温尼科特的假自体进行联系:因为长期处于挣扎企图唤醒母亲的「假装」之中,无法连接自己的感受,以致剩下一具躯壳。
这并非急性情绪带来的「解离」,但却是长期的「我」不存在于自己的身体里的感觉。这将造成个人连贯叙事的混乱,身份认同的乖戾与意义感的缺失: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贫乏、空洞,犹如行尸走肉。
被动
与此同时,这将造成一种长期、持续的被动感,因为一切行动并非自主、自愿,而只是被迫唤醒母亲的尝试。这种被动感同样将会带来一种最初难以被体验到的巨大怨恨,这份怨恨如此底层、巨大以致可能摧毁一切,这也是它很难被体验到的原因之一。
在咨询之中,如 Green 所指出的,这将造成一种「喂养分析师」的体验;咨询被还原成为了努力唤醒死亡母亲却从未成功的过程。事实上,咨询本身被「杀死」了,被拖入了那样一个「空白」之中。咨询继续,但是来访者既不能够真正依赖咨询师,也很难体验到「死亡母亲」相关的核心冲突。直到这一过程被觉察、讨论,才有可能带来真正的改变。
缺乏活力
另一个与之相关的主导感受是长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活力,即使生活本身是有序,甚至不断前进,看似富有成果;即使有时个体甚至可能进入过度兴奋的类躁狂状态。
这种缺乏真正活力也可能表现为:抛开表面上的种种活动,挥之不去的是一种底层的乏味、贫乏的感觉,无法感受到真正的「欲望」,通常以「随便」、「应付」、「凑活」这样的状态而存在。
因为缺乏活力,个体同样可能「性化」关系,无论是与人或物的关系;将表现为物质或工作成瘾,或者快速、强烈地坠入一段恋情。这些都让他们短暂地体会到一种虚假的活力,同样像是面对死亡母亲的兀自燃烧:只有足够热烈才有可能唤醒母亲,可结果却是,燃尽自己也无法得到死亡母亲的丝毫关注。
永不停歇
前文之中所说的类躁狂状态实际上就是面对死亡母亲的绝望努力,它是一种虚假的「活力」,内底更是一种面对死寂的极端惊恐,种种挣扎更是一种惊慌失措,或病急乱投医。
它与前面所说的「缺乏活力」是一体两面:一方面,个体表现出来强烈的驱动力、明确目标,以及持之不断的努力,另一方面,对待一切事物都显出并不在乎的状态,即使达成目标也不会真的带来欢喜或成就感,而是随即奔向另外一个难度更高的目标。
就算获得成就也根本无法填补空虚。实际上,就像 Green 指出的,因为死亡母亲带来的「空白」,个体倾向于使用智性追求作为弥补,通常都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是,人生最为惨痛的不过,幸福与成功并不相等,不可互相替代。
当然,这同样出于一种对于「死亡母亲」的认同:没有办法体会,当然更没有办法享受「过程」,没有办法真正地「活」。
希望犹在
意识到这一「空白」的存在,而不再使用种种努力逃离,是开始痊愈的前提条件。那一「空白」绝非真正的空白,而是包含巨大的但却不能表达甚至接触的怨恨与渴望。而之所以无法接触到「空白」,也是因为怨恨与渴望过于巨大,一旦释放,自我、客体、关系都将遭受冲击。
「空白」生成于一次又一次、长期而反复的互动的跌落之中,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样一个过程,总是勇敢向前一步表达变作永坠崖底的惨剧,「婴儿」被摔死了,灵魂也被轻风吹走,离开身体。
如果有人可以坚定耐受打开潘多拉魔盒的暴风、巨浪,如果有人可以在那里轻唤一声:魂兮,归来。
References
[1] 「死亡母亲」(the dead mother): 我的同学于琳琳将之翻译为「死妈妈」,也是一个直白且骇人的译法。
[2] Life Narcissism, Death Narcissism(生自恋,死自恋): 当然这一书名也昭示了 Freud 对于 Andre Green 的巨大影响
[3] On Private Madness: https://www.routledge.com/On-Private-Madness/Green/p/book/9781855751781
[4] 《偏执过程》: http://www.paranoid.net.cn/the-paranoid-process/content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