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
首先想要更新的一个消息是,「何苦开心」之前一直有在维护的「精神分析文献笔记库」由 wordpress 转移到了 Heptabase,以更加可视化且有组织的方式呈现,且更加方便地实时更新。「文献笔记库」与「阅读联想」同属精神分析内容策展,但是侧重各有不同,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兴趣选择关注。「文献笔记库」也将持续为「阅读联想」以及「何苦开心」的其他栏目提供营养。
点击这里前往「精神分析文献笔记库」
另外,我也在小报童开启了付费专栏「随愈而安」,这是一份精神分析式的自助手册,也是「何苦开心」的内容孵化器,你可以在这里查看更为详细的介绍,如果你喜欢我正在创作的内容,想要第一时间阅读孵化内容,或愿支持、鼓励我的持续创作,可以订阅「随愈而安」。
接到第一封信的反馈,我在考虑推荐内容的中英文比例,也在本期做了一些调整。另外,未来可能将要增加一个栏目,内容是针对传记的精神分析解读。如果你对于这以上改变有任何想法,都欢迎回复邮件告诉我。
一个主题
某一主题文献的摘要与整合,让真正的精神分析文献距离每个人更近一点,打破似是而非
「无助」是一种非常难以耐受的感觉;很多情况之下,只是因为想要驱赶无助,我们可能做出更多自我破坏的事情,而其目的只是为了找到一些其实虚假的「掌控」感。比如,为了避免遭受被抛弃的恐惧,所以首先切断关系;又或者物质滥用就和这一感觉极其相关(可以参考 Addiction, Helplessness, and Narcissistic Rage),而 AA 协会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提高人们对于无助的耐受。就像他们开始时总要念诵的祷文:
愿上帝赐予我平静,能接纳我无法改变的事。
我常说精神分析对于情绪理解的贡献在于接触那个早期、原始的部分,因此,我发现 A Genetic View of Affect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Genesis of Helplessness and Hopelessness 这篇文章格外有所帮助,因它恰是从新生儿开始讨论无助的发展过程,并且区分无助与绝望——前者是无法从客体处获得满足,后者是无法为自己提供满足。从还未分化的原始焦虑出发,经由愤怒、恐惧等强烈负面感受,而这些感受无法通过靠近或者回避客体减轻,最终成为无助。
另一有趣(但又相当合理)的发现则是,无助并不总是经由负面感受引发,过度兴奋而无法调节同样可能导致创伤以及无助的产生(On Excess, Trauma and Helplessness: Repeti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如同我在最新一期的播客「应对复杂时代的心智训练」之中所说,无助是常与创伤相伴的情绪。
回到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常常或多或少遭遇无助。无论是令人悲观的经济环境,是以选择躺平,还是面对复杂问题时的无法思考,就像撰写论文的拖延。焦虑与无助都是应对危险的情绪反应,但是无助甚至要更加「糟糕」,因为焦虑代表生存愿望,而无助则代表自我麻痹,因为危险是不能克服或者避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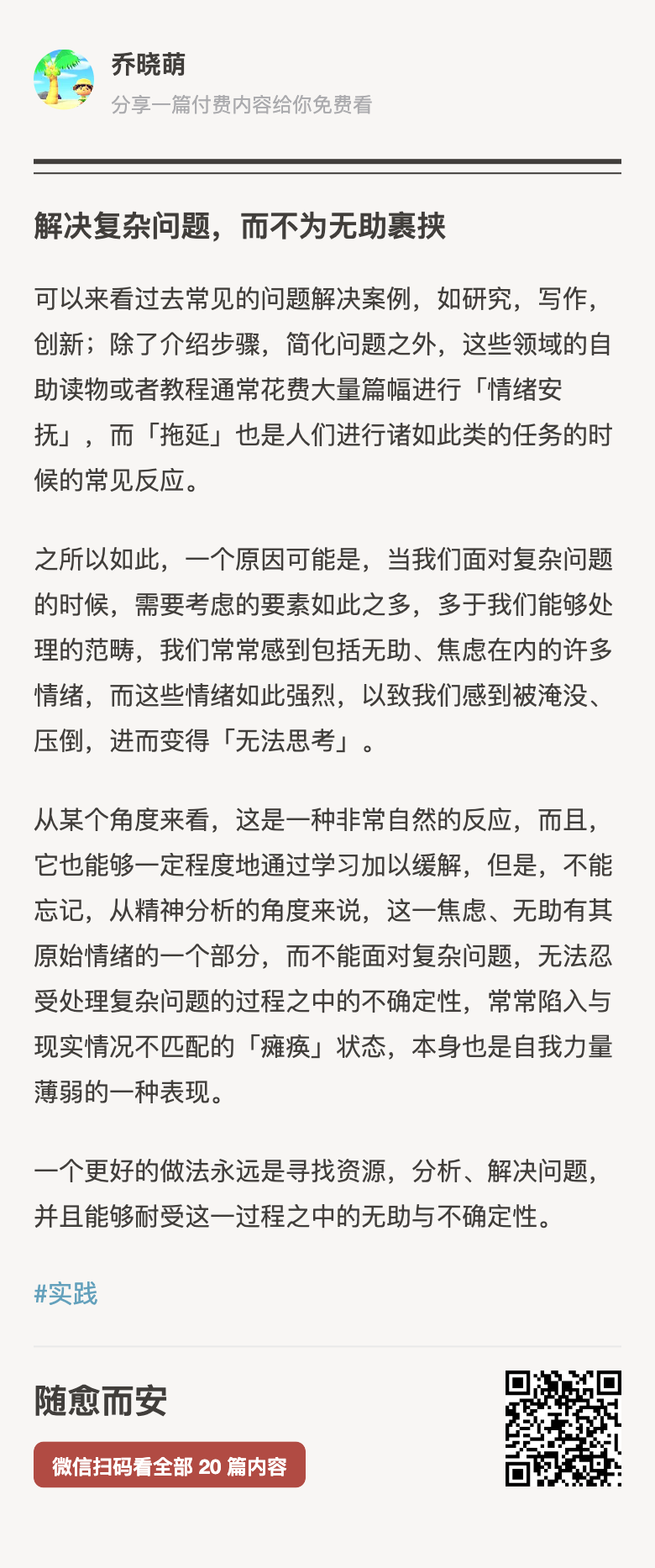
但精神分析是一种培养适应、灵活与创造的工具,面对不确定性,我们并不一定只能木僵、停滞,而也可能发展出来具有创新的解决方案。这一可能当然需要对于无助的耐受。
一组推荐
精神分析相关书籍,写作,社交媒体等内容推荐,3 - 5 条,可能与当期主题有关或无关。
并非刻意,但是本期的一组推荐部分还是和疫情有关。不过,正如方可成所说「长期的封锁对人的心理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和重视的」,这些推荐其实不是「过度讨论」,而是想要指向曾被忽略的关怀。
Freud and China
关注弗洛伊德伦敦博物馆的同学可能已经了解到了这个展览,这是博物馆今年相当重磅的项目。它在 2 月份开始,不过目前网路放出了更多内容,所以现在才向大家推荐。你可以看到弗洛伊德的中国藏品,由策展人牛津大学艺术史名誉教授 Craig Clunas 介绍的其中的五件藏品,以及它们如何展现了弗洛伊德的其他面向;一篇由 Clunas 撰写的策展有关的文章,若干与之相关的研讨会,博物馆页面同样添加「中文」,并且写道「弗洛伊德对中国很感兴趣」。
弗洛伊德对中国很感兴趣。他图书馆的藏品中包括英国作家 Una Pope-Hennessy 的《早期中国玉器》,1923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 Creel Herrlee Glessner 的《中国诞生》,是一部 1936年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普查记录。
弗洛伊德感到自豪的是,他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他 1933 年的中文版《精神分析讲座》也是他的收藏之一。
未来博物馆还将出版双语书籍《弗洛伊德与中国》,而此前也有蒋韬老师相关主题的著作出版 The Reception and Rendition of Freud in China。
不得不说,中国即将在精神分析发展之中扮演越加重要的角色:越来越多的候选人结束受训,正式毕业成为精神分析师,温翠芹加入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的教员行列,这些都是相当鼓舞人心的好消息。
《大瘟疫时期的压力和精神创伤》
疫情本身就是一种创伤,因此,应用创伤模型对其进行理解非常必要。《大瘟疫时期的压力和精神创伤》就是这样做的。这是一本非常简短的小书,但是包含许多重要内容,在介绍创伤相关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它讨论了疫情与其他灾难对于心理健康影响的比较,医护人员目睹病人丧生带来的「幸存者内疚」,网络环境对于心理状态的影响,疫情之下的心理治疗等。疫情回潮的当下,阅读本书或许能够让每一个人都对于自己更多一些理解和宽容。作者还有另外一本《大流行时期的心理状况》同样可以参考。
疫情中的封管控会对心理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篇文章来自我的同行庄淑婕及其伴侣王家醇,二人曾因合译《爱与岁月:精神分析视角下的爱情》而为人所知。作为身在上海的同行,他们体验到了本轮疫情的种种波澜,以及疫情之下咨询工作遭受的挑战。虽然我们的确已经看到了越来越多关于「疫情之下的心理健康」这一主题的分享,甚至包括我本人也曾与播客先生主理人 zack 做过一场直播,但是,这篇文章还是一次少有的具体详实的带有专业角度的论述。在此推荐给大家。
唯理中国线上课程 | 第三十五期:何为疯癫——心理病理学入门
我的播客「清醒梦」有一期叫做「大家都有病」,讨论的是去病理化的问题。此期唯理线上课程令人惊喜,也是因为对于「疯癫」的历史与哲学探讨。我欣赏它的课程介绍,因此直接做一引用:
理解「何为疯癫」是探讨「什么是(非)正常」这一问题的重要基础,更触及到「我是谁」的终极身份问题。在本节课中,我们将以「疯癫 / madness」为切入点,一起揭开精神疾病或令人害怕,或令人避之不及的偏见面纱,穿过层层阴暗的迷雾,看到哪怕微弱的,一丝明晰的曙光。
当然,本次推荐更多是想要引入这个视角,我与课程本身也毫无利益相关,如要报名还请读者理性消费,自行斟酌。
Critical Psychology
「何苦开心」曾经翻译过的「精神分析史」系列的出品方 Stillpoint Space 的新的系列 Critical Psychology,包括非常多的视角,音乐、角色扮演游戏、《鲸鱼游戏》,教练技术等,声称这一系列的使命是通过联系、探索和创新来重新构想 21 世纪的心理学。颇有一点「清醒梦」以精神分析的视角理解世界的味道。每集 30 分钟左右。因为每个人的兴趣不一样,所以非常 general 地推荐一下这个系列。我也没有每一集都看。
一位作者:Kenneth Newman
精神分析作者推荐,以人为单位的学习
Kenneth Newman 是另外一位带有强烈的自体心理学色彩的分析师,而且同样距离我并不遥远。他在 1996 年到 2002 年期间担任我所就读的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院长,是一名受人爱戴的督导与老师,被认为是「分析师们的分析师」。在他的讣告中,我读到一些非常熟悉的名字。
Newman 继承并且发扬了科胡特、温尼科特的许多理论,对其做出弥合与重要补充。比如,关于「假自体」(false self)这一概念,虽然后人有过许多阐释,但是,在我看来 Newman 的归因可以说是最为完整与精彩的:1)养育者长期无法适应婴儿引发强烈愤怒与无助;以及 2)养育者无法抱持这些强烈情绪以至婴儿不得不远离它们以及自发需求。
Newman 最为人知的概念是「可用性」,这一概念同样根植于科胡特、温尼科特,但是带有更多他本人的创造,而他也在多篇文章之中不断发展、深化这一概念,比如:The Usable Analyst: The Role of the Affective Engagement of the Analyst in Reaching Usability,Disclosure, Countertransference, and the Promotion of Usability,Countertransference: Its Role in Facilitating the Use of the Object,甚至包括将此概念活用至 A More Usable Winnicott。简单来说,「可用性」是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之后,儿童将不再把母亲视为全然可控的客体,而是能够分离的独立个体。
当然,许多人都曾在进入这一阶段的过程之中遭遇困难,而 Newman 和上一封信中介绍的 Tolpin 相同的是,他们对于这些困难都抱有极大同情与理解。Newman 认为,「治疗空间可被视为一个潜在的舞台,病人将在其中逐渐调动更深层次的需求和情感」,而分析师需要在治疗过程中逐渐变得可为病人所用。
除此之外,Newman 还是一位电影迷,并且常以精神分析的角度检视,许多文章就是由此出发。
如果你想要更加切实地感受他的风格,可以观看这则简短的采访,其中 Newman 的温暖亲切扑面而来,他所表达的还是自己的核心观点之一:
难以想象有些人长久以来的情感孤独。而我们希望能够让病人们感到「他们是被珍惜的」。
一些闲话
咨询师们的日常闲谈,不涉及任何来访者信息,3 - 5 条
精神分析是实用主义的。
摘自一段与适应性有关的讨论
心理学只强调自己是科学的时候,就失去了一部分人性。
摘自一段「有完没完」的「精神分析 vs 科学」的讨论
找一个人把你记住心上。
摘自同行刘珺关于心理咨询体验的分享
一点联想
万物皆可分析:以精神分析的角度摘录一些与精神分析无关的内容,3 - 5 条。
空间
空并不意味着「什么都没有」或者「零能量」。在很多情况下,它指的是一种状态,或「机前」,即生手之意:将来是被会内容填满的。在这一假设基础上,使用白即能形成沟通的一种有力能量。
——原研哉《白》
治疗
有兽医跟我讲说,这种小狗它从小被我送给别人,然后别人又把它退回去,其实对小狗会变成一种双重的创伤。当时我就跟我小儿子说没问题,我们把它疼回来,我们把爱回来。
——骆以军《我的小儿子,愿我们的欢乐长留》from《故事便利店第二季:小情歌》
客体
小黄鸭调试法,又称橡皮鸭调试法、黄鸭除虫法(Rubber Duck Debugging)是可在软件工程中使用的一种调试代码的方法。方法就是在程序的调试或测试过程中,操作人耐心地向小黄鸭解释每一行程序的作用,以此来激发灵感与发现矛盾。
——维基百科
沉默
无限的言说并不终结于聆听者的顺从沉默,而是通过言说者的参与式沉默而得到继续。参与式沉默不是一种言说已死的沉默,而是一种言说得以诞生的沉默。
——James P. Carse《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一个哲学家眼中的竞技世界》
共情
The deeper truth here is that Wordle thus trades on empathy rather than mere competition. It is not really a “competitive”game in the way that, say, chess is a brutal zero-sum bloodsport.Everyone understands that there is a large portion of luck involved in Wordle, and anyway almost everyone “wins”every time. Its most fundamental – and, in these times, radical– message is that sometimes we can have nice things, and we don’t have to take them away from others to have them. If only more games – let alone life– were so.
更加深刻的是,拼字游戏 Wordle 由此达成共情交易,而非只是竞争。它并不是一个像国际象棋残酷零和血战那般的真正「竞争」游戏。每个人都知道 Wordle 很大程度上和运气有关,而且几乎每个人每次总会「获胜」。这款游戏传递的最为基本的信息是,有时我们可以拥有美好的东西,而我们不必为了拥有这份美好而将它们从他人手中夺走;而这一信息在今天已经显得激进。如果更多游戏是这样就好了。更不用说如果生活是这样就好了。
——Steven Poole from Trigger Happy in Edge 2022 April
谢谢你的时间。
我们下次再见。
乔晓萌
2022.6.7
